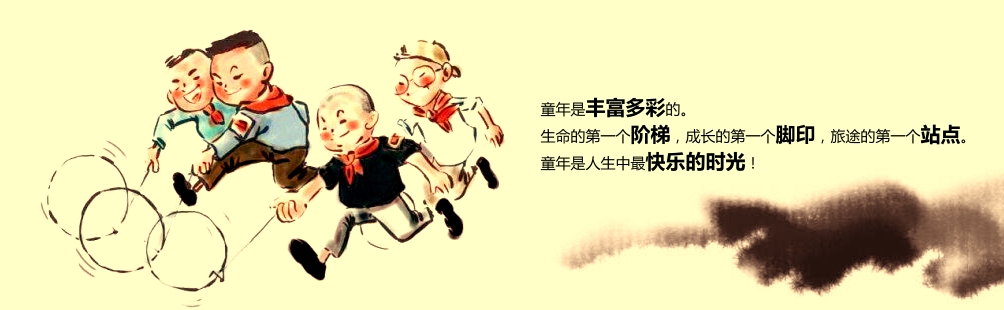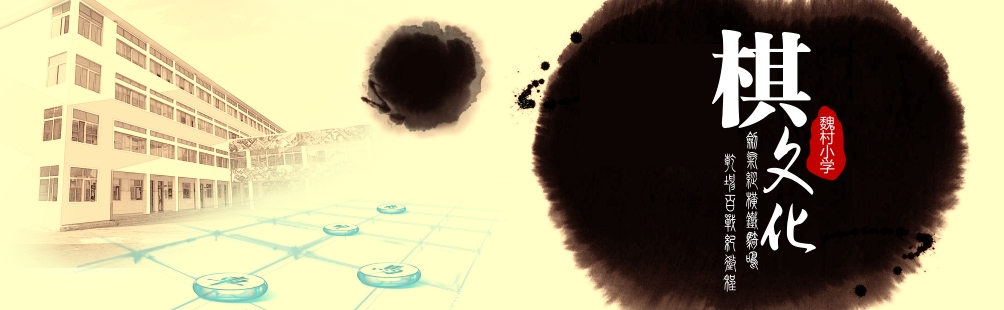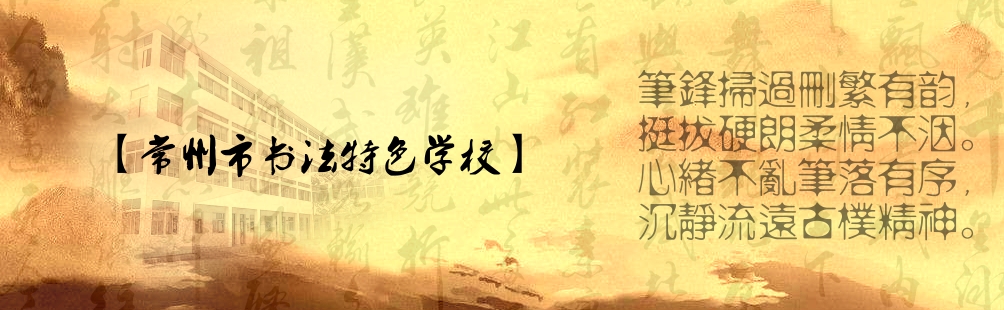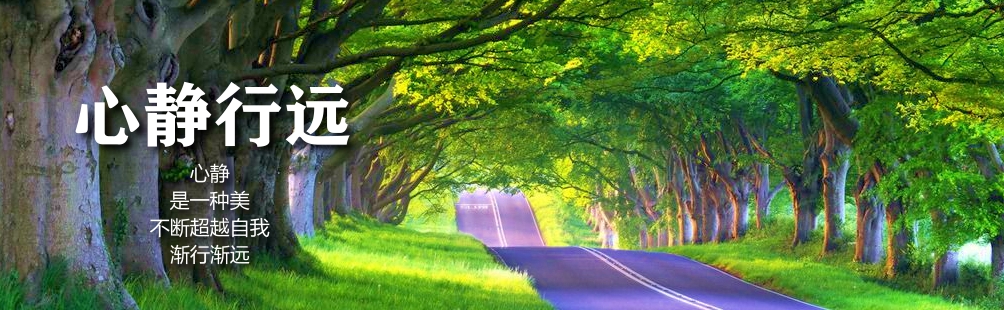读《蛙》有感
读书就像吃饭一样。你小时候吃的什么饭什么菜你不一定都能够记得,但是你吃的那些饭,它们慢慢的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不是么?读书,就像吃饭一样,慢慢丰富你的知识,开阔你的眼界,那些知识会融进你的骨血之中,让你变得更有气质和修养。
对我来说读书是源于兴趣,一些经常看书的人会享受阅读,当多体验阅读,就能感受到它的作用,感受到它对你的改变,感受到其中的美好了。
《蛙》是中国当代作家莫言创作的长篇小说。这部小说以新中国近60年波澜起伏的农村生育史为背景,讲述了从事妇产科工作50多年的乡村女医生万心的人生经历,也反映出中国计划生育的艰难历程。小说秉承了作者乡土文学的一贯风格,以细腻的笔触、朴实的文字落脚于中国社会的一隅。
莫言小说《蛙》主要讲述的是乡村医生“姑姑”万心的一生。“姑姑”的父亲是八路军的军医,在胶东一带名气很大。“姑姑”继承衣钵,开始在乡村推行新法接生,很快取代了“老娘婆”们在妇女们心中的地位,用新法接生了一个又一个婴儿。“姑姑”接生的婴儿遍布高密东北乡,可丧生于“姑姑”之手的未及出世的婴儿也遍布高密东北乡。姑姑一面行医,一面带领着自己的徒弟们执行计划生育政策。让已经生育的男人结扎,让已经生育的怀孕妇女流产,成了“姑姑”的两件大事。
《蛙》是蝌蚪讲给日本友人杉谷义人的关于姑姑的故事。当然,蝌蚪本人,小狮子,等也是本书贯穿始终的主要人物。
初读这本书时,我很压抑,感到小说里那些情节太过残忍。因为时代不同,我甚至无法理解书中的“姑姑”为何做事要那么绝,已经达到了六亲不认的地步。直到我读到“姑姑”在戏剧性地嫁给了郝大手之后,我才开始慢慢地有些了解她的苦衷,她的身不由己。
全书的主人公——姑姑,名字叫做万心。万心矛盾地拥有着两种身份:一种是乡村医生,一生接生婴儿近万名,人称“送子娘娘”;另一种是坚决执行计划生育国策的计生干部,人又称之“杀人妖魔”。对于万心来说,却必须做到统一,她的一生因而活在无法逃脱的极度矛盾和痛苦之中。万心卫校毕业,一辈子跟妇女打交道。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她是接生员,无论多么困难的分娩,只要经她接手,就会转危为安,就连母牛难产,大家都请万心出马,那时候,她是四里八村妇女的大救星,活菩萨。
然而到了八十年代,她一下子由天使变成了魔鬼。张拳的老婆因她溺死水中,她侄子万足的老婆王仁美被她大义灭亲引产失败大出血死了,袖珍美人王胆在被她追赶的途中所幸生下女孩陈眉,但王胆的命也没保住......
后来她途经芦苇地,被无数的蛙围攻,撕碎衣服,咬破耳朵,被黏液喷得到处都是,再后来,她夜夜失眠,猫头鹰的叫声被她幻化成蛙的惨叫,她觉得这是那些无辜的生灵来讨债了。“蛙”,就是“娃”啊,万心的这双手,接生了上万个娃,又残害了多少个娃啊!如果她不仅仅是一个妇女工作者,如果她能在当嫁的年纪嫁掉,在该生的年纪生产,她的心就不会这么硬,这么冷。
可惜,她年轻的时候与那个英俊的飞行员擦肩而过,后来在她徐娘半老的年纪里,戏剧性地嫁给了郝大手,一辈子接生了上万个孩子,却没有一个属于她,这也许就是对她作恶的报应吧?
书中的“我”,即为“姑姑”的外甥——万足(即蝌蚪),他的第一位妻子就是被“姑姑”大义灭亲,强行引产致死;而他后来的妻子,则是“姑姑”的徒弟——“小狮子”,她也是从参加工作起,就一直跟随“姑姑”做着接生和引产的工作,或许也正是因此,她也是一直都无法生育。
《蛙》是一部对中国当代乡村的现实看得很深、思考得很透的作品。
在这些思考的背后,则是对中国现代命运的深切忧虑和反思——这也是莫言小说的一贯主题。
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在中国具有合法性和必然性,因为人口是一个国家走向繁荣的前提,而控制人口又是后发展现代国家实现艰难的现代转型的无奈但必要之举。生育,是人的基本权利;而控制生育,又是人实现理性生存的必要手段。
在新时期以来的文学作品中,计划生育一方面被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进步事业”得到充分肯定,另一方面,则成为90年代以来主旋律乡土文学突出乡村基层政治尴尬现状和困境的点缀性情节。于是,被不理解、不支持的农村群众撵得到处跑的“乡镇干部”形象,就在几分黑色幽默的喜剧色彩中,将计划生育政策与人性的冲突轻松地嫁接为“分享艰难”的主旋律阐释。
读《蛙》,读者会时时感到残酷:一是小说情节和人物命运的残酷,另一是莫言客观冷静地书写他人灵魂深处极致痛苦的残酷。高密东北乡不仅仅是故事发生地,而且是一个泛指意义上的区域。在计生国策推行之初,中国有无数个东北乡,万心这样的计生干部也有许多个。莫言的书写因而有着广泛的代表意义和现实意义。
《蛙》里的一切无不指向“生命”二字,主要人物的名字、故事情节,甚至刊物的名称都在为生命鸣唱。这一切寓言式以及象征式的经营手法,把小说推向一个更高的层次,也即观照生命、歌赞生命、敬畏生命。